刚刚过去的2023年,发生了一件没有引起太多读者关注,却引发书业热议的事,一直广受好评的文学杂志《巴黎评论》的系列电子书从微信读书下架了,将全面转向单品销售模式。据巴黎评论编辑部回应,原因是微信读书不支持仅以“单品购买模式”销售他们家的电子书,要求必须在参与“付费会员畅读计划”的基础上,才能做单品销售,引发了《巴黎评论》的不满,导致双方合作破裂。

对于互联网阅读平台热衷的“付费会员畅读”商业模式,其实出版业一直怨言颇多,尤其是收益核算机制完全不透明问题。《巴黎评论》的编辑曾在某书平台上深入谈及过,微信读书向他们提出按图书的阅读页数甚至字数计费,却没有明确告知具体的计算数据,以及每页内容最后售价多少,整个结算过程几乎是在黑箱下操作,版权方太过被动,且获益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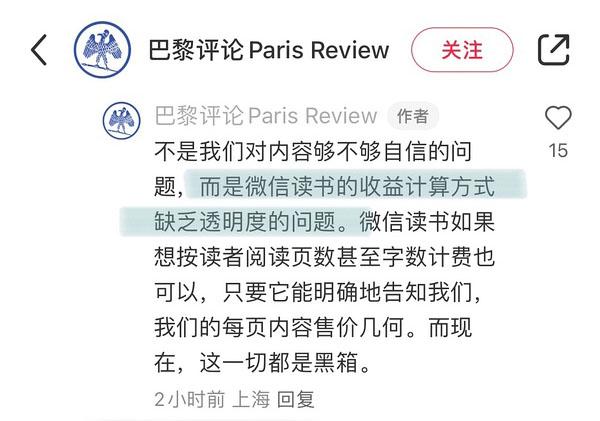
所以,即便他们自身内部对微信读书的去留还存在分歧,也毅然决定不再参与任何“付费会员畅读计划”,往后要以全平台统一定价,在支持“单品销售”的诸如豆瓣阅读、掌阅、当当云阅读等平台上,以单品形式销售自家的电子书。
这次事件的发生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在图书数字化步入当前阶段,“付费会员畅读”与“单品销售”这两种电子书的主要商业模式,就像两列已经驶向道岔的火车,即将奔向不同的目的地,出版业要上哪趟车,关乎的是整个图书行业的未来发展走向。《巴黎评论》下架事件只不过恰时反应出出版业内部在这两种模式的选择上,已经逐渐产生分化。如今出版业不得不开始思考:究竟哪种商业模式,对书业长足发展更有利?
一、付费会员畅读,志不在图书销售
“付费会员”模式是互联网内容生态探索出来的重要商业模式,这些年通过各大影音平台已经养成大批有付费习惯的互联网用户,“付费会员畅读”搭上内容付费这趟车不算顺便,更像精心布局。无论网文或是版权图书,文学创作一直是支撑庞大内容生态的“源代码”,版权图书是互联网必须收编的一个内容分支,如果脱离“付费会员”模式,仅按单品来一本本销售,就违背了互联网企业自身的利益诉求。因为对于互联网企业而言,“付费会员畅读”可以最大化发挥版权图书的内容价值,来巩固平台流量,以此帮助互联网开展更多的盈利业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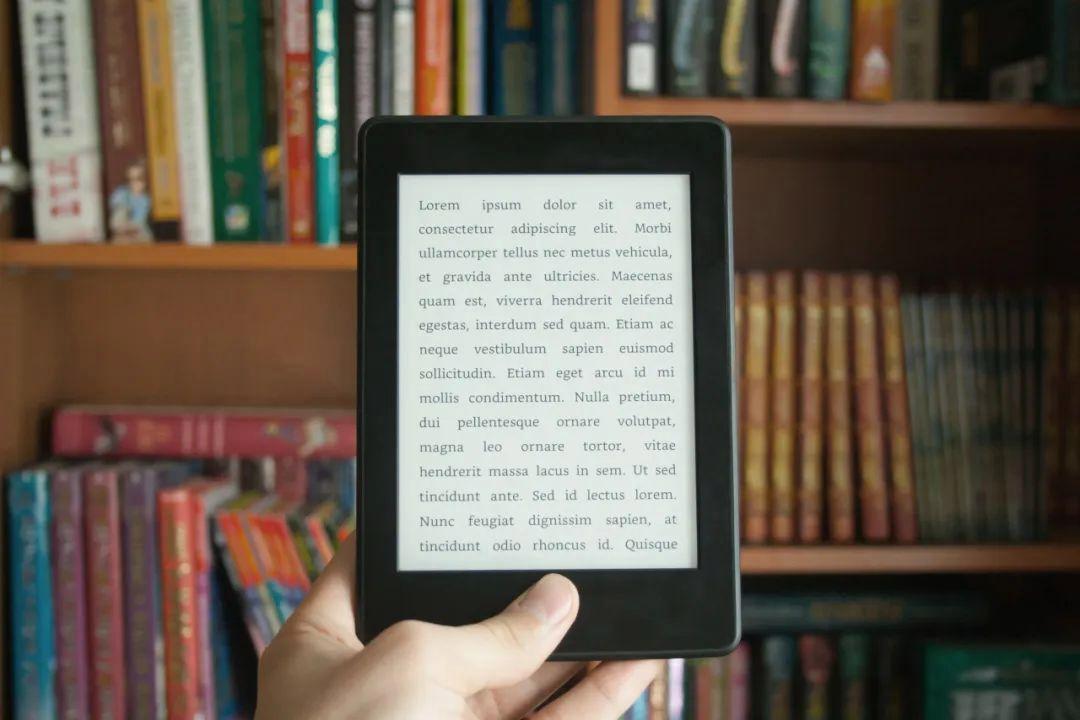
再者,以传统图书出版路径获取版权的方式,对建设内容生态来说成本负担过重,为了实现更大盈利,平台踏上自有版权开发是必由之路。在国外亚马逊已经趟过“自出版”这条路,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在2019年全球作者从亚马逊自出版获得的收入就超过3亿美元,自出版业务已经成为亚马逊的重要收入来源。
近年国内各平台也有布局自有版权的苗头,如微信读书就在去年9月开始陆续上架了46本微信读书出品的电子书,这些书一上架就抢占了飙升版、新书榜的前几名,拥有平台倾斜的流量与热度。再观其他版权图书,不仅要先被平台自出品的电子书分走一波流量,还要面临随着上架版权图书数量越多,每本图书被阅读次数与时长越少的苍白现实,结果就是平台为每本图书支付的费用不断减少。
“流量为王”的时代,流量平台甚至不需要担忧如何向提出质疑的出版社解释为什么要暗箱结算?平台自出版的开发边界又在哪里?因为有的是前赴后继,愿意与虎谋皮的“胆量者”,更何况在这套“聚集内容资源,为流量提供服务”的商业模式中,出版方只是其中一个参与环节,甚至不是决定性环节,随时有被替代、优化的可能。所以这种商业模式,究竟得利的是谁?对出版业可持续发展又助益如何,需要业界同行自行甄别。
二、单品销售,为什么会成为选择?
图书采用单品销售模式来经营,是书业运作的日常,但是应用到电子书上,许多人就没有底气了,觉得新科技总得搞个新模式,才叫革新。然而太阳底下没有新事物,有些规律被总结出来就是有其亘古不变的道理。图书为什么要按卷、按册、按本来卖?思想创作本身难以衡量、估算价值,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是通过载体切割内容的方式做计算,卷、册、本都是统一标准的计量单位,使各种思想成果能以统一标准被市场计价。
“付费会员畅读”的问题之一,就是互联网平台试图打破书业公认的计价标准,建立另一套有利于互联网行业的新计价标准,触及了书业的根本利益。原本能以“单本”书计的内容价值,最后被切分成一页一页、一秒一秒去计价,无形拉低了所有作品的价格,就是想把正本书谈成“几张纸”来采购。
相比单品销售模式对书业持续发展更有利。原因有很多,这里谈谈三点:
第一,通过单品销售,出版社不仅能以清晰的销售数据结算收益,还能掌握到每本电子书的实际市场行情,有助于出版业自身积累电子书市场的数据模型与经验,这样才能为数字时代书业的全面转型积聚行业力量。
第二,且不论单本销量有多少,至少卖一本能“算”一本,而不是打着在线阅读的名义,赚着低廉的点击费用,还要在授权到期后被缓存到书架的用户白嫖电子书。浏览一些平台用户的讨论,就能看到关于某些平台即使图书下架,用户依然可以阅读的言论。如果是技术原因,那说明这种平台“在线阅读”模式本身就存在技术漏洞,又怎么保障出版社的利益?
第三,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单品销售实质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保障内容创作的质量。按读者阅读页数、甚至字数计费,对内容创作产生的影响,参看网文写作、短视频生产就能知道。所谓的黄金三章、前三秒定律,都是通过开头抓眼球的方式来定调内容生产的,导致整个内容创作群体越来越浮躁,许多作品都陷入模式化、同质化的迷障,真正的好内容又如何能够被挖掘出来?
图书销售虽然是一门生意,但是多数从业者总归是抱着一丝想要捍卫“精神国度净土”的理想。如果仅以“流量”思维论创作,当阅读刺激性的低质量内容成为所有人的阅读常态后,将极大地扼杀掉“人”的逻辑表述和深度思考能力。如果书籍不再带来成长,仅用于娱乐,那才是书业的真正死亡。
所以,我们说“单品销售”模式对书业发展更有利,只是当前各平台对“单品销售”模式的理解有本质差异,导致市场还存在乱象。
三、此“单品销售”,非彼“单品销售”
谈论单品,就需要对单品交易过程的权利进行界定。照纸质书的常理,读者购买了按单品销售的电子书,就应该拥有这“本”电子书的所有权,可以自由处置它,这是现代书业发展以来的普遍认识。
互联网流量上常见的一种“单品销售”模式,是通过获得版权方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上的授权,然后将版权图书的内容当成“一本”独立的电子书进行销售,这在法理上其实是说不通的。因为《著作权法》明确规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限范围,是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

也就是说,平台方不能在授权平台以外的地方为读者提供电子书内容,读者也不能脱离授权平台来阅读所购买的电子书内容,甚至并没有在法律层面上拥有过这“本”电子书,更谈不上单品交易,只是以卖单品的价格,让读者享受一把授权期限内的在线阅读服务,本质与“付费会员畅读”的阅读方式是相同的。
这个问题的微妙之处是,如果作者、出版社、平台、读者没有任何一方追究,也就悄无声息地揭过,该卖卖,该用用。一旦有人提出异议,都是可能判决赔偿的,所以通过“信息网络传播权”卖单品电子书,本身潜在一定的法律风险。这些年因“信息网络传播权”解释不清产生的版权纠纷案,不在少数。
另一种“单品销售”模式,是由福建新华发行集团联合厦门正观易知书业科技提出的,选择以“复制权”“发行权”授权来做数字图书的网络出版。这种模式通过“出版”让数字图书的“书”成为真正意义上可以独立交易的商品,它的经营模式在法理上受到《知识产权法》的权利用尽原则保护,所以出版社一是可以将这种出版过后的数字图书像纸质书一样销售给读者,读者可以合法占用、使用所购的数字图书,没有售后的法律风险顾虑;二是这套“单品销售”模式,还配备了服务于出版社的“数字图书出版发行云平台”,据说平台可以支持出版社自主出版、管理、追踪所有数字图书,获取第一手的运营数据,以及支持以版税制结算每一本数字图书的收益……如此评估下来,通过“复制权”“发行权”出版数字图书开展“单品销售”的机制,对出版业来说其实会更有利。
资本、技术进来后,这几年书业的变化是巨大的,纸书销量逐年下滑,守着老路子肯定是行不通的,出版业在电商、流量平台的裹挟下,看似参与了不少创新模式,却缺乏主导性和主动权,很多决定更像是顺水推舟,思考的并不够深入,以至于出版业慢慢步入如今两难的“死胡同”。《巴黎评论》的下架事件,或许只是一个开始,后续出版业与互联网业的矛盾,在利益分配越来越不均的局势下,只会不断激化,选择何种商业模式,如何进行自救,是每一家出版社都逃不开的发展命题。
电影《流浪地球》这样说过:“起初,没有人在意这一场灾难,这不过是一场山火、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深以为然,也以此为戒。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吕岭路1819号精图数码大厦A-502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吕岭路1819号精图数码大厦A-502
 0592-6300088
0592-6300088
 zgyz@geeboo.cn
zgyz@geeboo.cn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闽网文〔2022〕1740 一 072号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闽网文〔2022〕1740 一 072号

